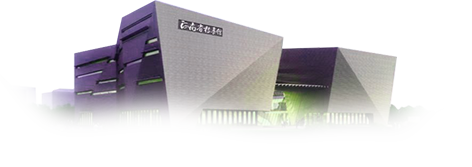红色故事之灭蝗
蝗虫真是个怪物,没有的时候你无论如何也找不来一只,有的时候你不知道能有多少,它们成群结伙,遮天蔽日。绿油油的庄稼苗叫他们一闹就没了神气,变成光秃秃的一炷香。老百姓最讨厌这东西,可又没有好办法对付它,只好眼睁睁地望着它胡行。
宫前雁翎关一带闹蝗虫,老百姓愁得连饭也吃不下。他们怎么能吃得下呢?山里人,穷汉多,出死力,种薄地,好年景能弄个糠菜半年粮,像今年这样,别说吃了,光租地就把他们压得出不来气了。宫前街空荡荡的,仅有的几家店铺也关门闭户,只有几条狗轻轻地走来走去,有时张开嘴伸伸舌头,有时低低地叫两声,显然这东西也饿急了。突然一声长嚎震动了宫前街:“老天爷,你发发慈悲吧,可怜可怜我们吧!”各家的门板劈里啪啦一响,一个个干瘦的老婆、媳妇走出屋来,站在门前。这时,从街西头走来一个瘸老汉,他双手捧着香炉,那几缕线一样的青烟在他脸上绕来绕去。天气已经热了,他却穿着一件说黄不黄、说白不白的破棉袄,肩头、前胸挂着几朵灰灰的棉絮,他仰着脸往前走,行动是那样缓慢,神态是那样迟钝。“尤二是到堂庙烧香哩,三天了,都是这样。”望着他颤颤巍巍的身影,人们一片叹息,泪窝子浅的老婆婆说着说着就流出了泪儿。蝗虫给人们心灵上撒下的阴影太沉重了。
初春的一天,从南山下来一队人马,一色的灰制服。他们来到宫前街,背包一放,就开始工作,不一会儿,大街小巷就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。那宽窄大小不等的纸张上写着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!”“团结起来,共同抗日!”“共产党、八路军,为人民,爱人民”“减租减息,发展生产!”……各家各户的房门都打开了,人都涌到了街上。看见刷标语的人缺凳子就有人回家去搬,有人干脆把梯子搬出来靠到墙上,还有人把铁锅端出来让战土们喝水。这里没人指派,各人按着各人的心意办着各人能办的事儿。彼此那么亲密,虽不开口说话,但你能通过那眼神那动作知道他们的心是相通的。
在一面光洁的墙壁上,一个穿灰制服的人正在用白灰水刷大标语。许多人在看他写字,那字苍劲有力,写出了人民的心里话。尤二一下午都跟着,看到白灰盆里缺水就赶紧打来半桶;移动凳子,他先摇晃两下,看看是不是站稳了。写字那人细条条的个儿,大大的眼睛,白白净净的脸盘,长得满秀气,凭那潇潇洒洒的字儿,大家知道他肚里学问深着哩。他对老百姓非常和气,一边写字一边还和老乡说话,通过谈话宣传共产党、八路军打日本的新鲜事儿,听得人都不眨眼地瞧着他,胆大的尤二还和他说笑话。他那眼里有水,一眼就能看出尤二是个光棍汉,还故意问他老婆给他做什么好饭,惹得大家哄的一下笑了。可他并不笑,还说尤二一定会讨到一个年轻漂亮的好老婆。此间有人请示工作:“张区长,住的地方找好了,你去看看吧?”
他停住刷子,扭过脸笑着说:“不用了,你看着办吧。”
“吃饭问题咋解决?”
“找保甲长商量一下,先派到老乡家吃两顿。”
来人敬了一个礼离去了。人们都用惊异的目光回望着他:这么年轻就当区长!
傍晚,街中的一家院子门口挂出了一块木牌,上面写着:陕县宫前抗日民主区政府。
宫前街西头,有一座整洁的四合院,漆黑的大门紧闭着。突然,一个中年汉子跑到门前,急促地拍起了大门。
上房的门开了,从屋内走出一个人来,个头不高,看样子有50多岁,留了几根稀疏的黄胡子。他叫郝三娃,是宫前一带很有名气的土财主,大儿子在县城教书,二儿子在民团背手枪,在乡民眼里是很有点横劲儿的。他穿着一件蓝绸长袍,上套一件浅红缎子马褂,头戴一顶青丝小帽,左手托着明晃晃的铜质水烟袋,右手拿半截纸媒儿,他站在台阶上吹燃着纸媒儿,对着烟锅儿呼噜噜吸了一口烟,才懒懒地说:“谁呀?”
“三爷,是我,狗儿。”他步下台阶,开了大门。
“三爷,保长说咱家管5个人的饭。”
“什么人的饭,敢派到咱家,你去对他说咱家不管!”
“三爷,你老还是熄熄火吧,这回来的不是民军,也不是便衣队,是穿灰制服的八路军。”
“八路军?来了多少人?”
“眼下只有二三十人,谁知以后会来多少呢?”
“是过路还是常住?”
“看样子不像过路,区政府的牌牌都在连生家院子挂起来了。”
“噢,是这样。”他低头思谋了一会儿,果断地说:“狗儿,吩咐下边准备5人的饭菜,饭要热要好。”
“知道了。”狗儿离去了
山,从来就是这样,它不管你乐也不管你愁,总喜欢把自己那漂亮的面孔展示给人们。五月的山已经卸尽冬装,翠生生的绿意简直能使人醉,星星般的小黄花点缀其间,更给大山增添几多鲜活的姿色。
这山,他已经爬过几次了,可他像没个够,今天早晨又上去了,看来他和大山结下了深厚的情谊。他似乎觉得他应该关心它,保护它。党叫他来当区长,他一定尽职尽责,要把群众团结起来,鼓动起来,搞好生产,支援抗日前线。他从山上下来,又到前街后街转了一遍,当他回到区公所时,太阳已经一杆多高了,可村子里却还是一片宁静。他感到有些怪,昨晚开会讲得很清楚,今天早上一起行动扑打蝗虫,怎么这时候了,村里人还是紧闭门户,难道他们睡了一晚上把什么都忘记了?就是有人忘记了也不至于全村的人都忘记呀,他摇了摇头。
有人已经知道他叫张志杰,1937年入党,曾担任过中心县委书记,是个大“官”。这次从延安到豫西来开辟抗日根据地,党组织分配他担任宫前区委书记兼区长。他知道宫前是豫西二地委的边沿,三面临敌,常有日伪武装和顽军民团骚扰,能守住宫前这块阵地就是支持和保护了豫西抗日根据地,任务是十分艰巨的,党组织把自己安排到这里,是对自己的信任和考验。他到这里后发现,群众比他想象的要苦得多,在日本鬼子和汉奸武装的压榨下,人们几乎是无法生活,如今又遭蝗灾,更是冰上加霜。他决定先从扑打蝗虫入手,消除人们心理上的负担,群众才能发动起来搞抗日。
正在思索,区政府走出了一群人,他们手里挥舞着细长的柳条,看样子是准备上山的。张区长转身来到他们跟前,笑着说:“光咱们这几号人,蝗虫能打到啥时候,你们赶快分头去动员群众,只有大家都起来,才能扑灭蝗虫。”
他们点点头,笑着,唱着,往村巷里走去。
不一会儿来了些群众,张区长不太满意,说:“怎么就你们这几个人,大家伙为啥不来?”
“张区长,我们老百姓没打过蝗虫,都不想来。”
“我们来也只是想看看,蝗虫能飞能蹦,又那么多,人能打吗?”
“怎么不能,只要我们大家心齐,蝗虫是会被消灭的。没上阵心先怯怎么行,要鼓起勇气消灭蝗虫。”张区长说。
张区长领着乡亲们往北山走去。
忽然,从前边路口窜出一条汉子,他伸开双臂拦住去路。大伙一看是尤二,不由得笑了:“尤二,你发啥疯哩?”
尤二并不发笑,一脸冰霜,说:“大家听我一言,蝗虫打不得呀,它是天上玉皇大帝派下来的,打死蝗虫于我们不利。人老几辈了,谁见过打蝗虫,千万不敢打,打蝗虫要遭孽,要出天灾人祸,要断子绝孙。”
本来大家就犹豫,又经他这么一胡闹,心里更没底了。张区长没料到尤二会来这一手,他走上前对尤二说:“你从哪里听来的胡话,瞎说些什么?”
尤二扑通一声跪倒在张区长脚下,说:“张区长,你们来到宫前,我们欢迎,可你不该领着人马打蝗虫呀,那是神物,打它们要招祸哩。张区长,你可怜可怜我们这些小民百姓吧!”
“尤二,你起来,不许胡闹。”张区长看着乡亲们将要走散,忙丢下尤二,对大家说:“乡亲们,不要相信他这胡言乱语,蝗虫是自然界的一种生物,不是什么玉皇大帝派来的神物,况且玉皇大帝谁见过,它本身就是一种迷信,是根本没有的。大家不要受他欺骗,还是到地里扑打蝗虫要紧,咱不能眼看着庄稼被白白地遭害。”
这时,尤二倏地一下从地上蹦起来,指着张区长说:“你才是胡说哩,你竟敢说没有老天爷,这还了得!我问你,没有老天爷咋会黑了明了?没有老天爷咋会有龙抓人?前年后沟的小拴不就是被龙抓了吗?你说我骗人,我在这宫前街生活了几十年,我骗过谁了?其实你才是骗人哩,你说你是打日本的共产党、八路军,你为什么不上前线,不到有日本人的地方去?钻进这老山窝,连个鬼子毛都看不见,你打谁哩?你叫大家伙儿打蝗虫,你们穿着军装拿着枪说走就走了,可我们往哪走!惹怒了老天爷,降个什么灾,还不是我们来受哩。乡亲们不要跟他走,蝗虫千万打不得!”
那时候的人,信这,有啥法。望着纷纷走散的人群,张区长感到无能为力,他心里很痛苦,却没有良策。蝗虫是野物,不是神物,他清清楚楚,明明白白,可是任你浑身是嘴你也不可能去向每一个人解释,就是能解释,他们听吗?
忽然看见尤二还呆呆地站在面前,或许他意识到了什么,样子像个做错事的孩子,浑身里透着悲哀。在众多的山民里尤二要算最可怜的一个,他很小的时候,父亲被抓壮丁一去不返,母亲又得了绝症,为葬埋亲人他借了郝三娃50块现洋,从此他就跌进苦海里,整年劳累也还不清这笔阎王债。他了解他,今天这事不能怪他,他没有觉悟起来,自己有责任帮助他。想到这里,他肚里的气消了,他走过去亲热地拉着尤二往区公所走去。
张区长带领着乡亲们闯进郝三娃家院子,这在宫前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,农村人爱瞧热闹,男的女的,老的少的,能挪动的人都不肯放过这个难得的机会,一时间将郝家大院围了个水泄不通。
此时,郝三娃正躺在椅子上呼噜呼噜地吸水烟,忽见乡人像流水一样涌进自家院子,身子不由得软了,那铜水烟袋一歪,咚的一声掉到地上,突然他“叭叭"抽了两掌,才没有使自己倒下去,他撑着身子直起腰来,稍稍一静才走出屋去。
他双手抱拳,弓身施了一礼,说:“不知张区长和乡人光临寒舍,有失远迎,罪过,罪过。”
“你很会在后台演戏,今天倒要把你请到前台。张区长轻蔑地一笑,走近郝三娃厉声问道:“郝三娃,我问你,蝗虫是神物还是野物?”
郝三娃一听这话,心里明白,事情是包不住了,他就转了个大弯,顺流而下。于是浅浅一笑说:“区长大人息怒,我当为了何事劳你大驾,却原来是区区小事。蝗虫嘛,那自然是野物,野物。”
“既是野物,该打不该打?”
“蝗虫遭害庄稼,为何不该打?打得的,打得的。”
“你这人好忘性,昨个夜里你是咋说的?”尤二人模人样地走了出来,往日那副邋遢样儿全不见影了。
“昨个……我说什么来着?”
“你不用打马虎眼。你让我给村里人传话,说蝗虫是玉皇大帝派下来的神物,是打不得的,打蝗虫要遭报应。你还说不要听那个姓张的话,共产党这个区政府是兔子尾巴长不了。”
郝三娃像被火烫了一样,立时跳了起来:“一派胡言,尤二你个无赖!”
“郝三娃,你才是个真正的无赖。”尤二一下子冲到郝三娃身边,指着他大声吼道:“我不过是穷,不过是没老婆吗,可我是怎么穷的,还不是让你给刮的。在咱这宫前街谁不知道,我能吃苦,做得一手好庄稼。你会干什么?你会锄地?你会下种?你什么也不会,只会和你那小老婆玩,看见村里有个好女人,你夜里连觉都睡不着,想个孬点也弄到你屋里玩几天。要说无赖,你才是个不掺假的无赖!”反了,反了,平日俯首听命的尤二,竟敢对我这样不恭。可此时此刻又能将他怎样,若再搅下去,说不定还会生出什么不测之事哩。于是郝三娃忙转过身对众乡亲陪着笑说:“乡人都是通情达理的,莫要与尤二一般见识。”
“尤二说的是实话,你不是对我也说过蝗虫是神物,打不得吗?”
“你也让我给大家传话。
“你为什么不让打蝗虫?”
郝三娃见抵赖不过,忙说:“乡里乡亲的还能不知道我这一脑袋迷信,平日里就信神信鬼。”
“你真迷信吗?我看其中有诈”。张区长接着说:“乡亲们,谁家租种郝三娃的地,请举手。”
一只只手臂举了起来,张区长瞅了瞅,说:“还真不少哩,大约有百分之七十的人都租种他家的地。我再问大家一句,如果今年颗粒无收,他家的租子是不是可以不交或少交?”
“少交一颗也不中!那年大旱,人都饿死了,他还逼债哩。”
“甭说少交,就是迟两天都不中。”
“说收租,心狠着哩”。
“对了,这就看出郝三娃的用意了。他不让打蝗虫是把我们往沟里推的。大家知道他是靠地租吃穿,如果蝗虫把庄稼啃光了,我们拿什么给他交租?我们还吃什么?我们怎么生活?不用说,我们穷得更惨了。这就是郝三娃不让打蝗虫的真正用心,说封建迷信那是假哩。”
张区长的话把大家的心点亮了,望着眼前这个郝三娃,祖祖辈辈受剥削受压迫的怒火一下子迸发出来了,大家纷纷举起拳头,怒吼着:“打死这个狗日的!”
尤二不知从哪儿弄来一根粗壮的磨棍,高高举着冲了进来。眼看着乡人像水一样压了过来,郝三娃心里很有些怕。不过,一想到儿子曾对他说过的话,他就松了一口气:现在是对外,还不到对我的时候,看你们敢把我咋样!尽管如此,他的身子还像筛糠一样,不住地抖动。
在这急剧突变的时刻,张区长飞步上前,一伸手臂撑住尤二的磨棍,大声说道:“乡亲们,我们今天走进郝家大院主要是弄清蝗虫该打不该打。至于郝三娃,那就要看他以后的行动,如果改邪归正,拥护抗日区政府,我们是欢迎的;如果继续和政府作对,捣乱,我们是饶不了他的。”说到这里,他挪动一下身子,往高处站了站,说:“乡亲们,我们初到此地,受到乡亲们的热烈欢迎,我表示感谢。至于我们来这里干什么?我已经讲过几次了,可是乡亲们还有些糊涂认识,今天我再讲一遍。一句话,我们来宫前是抗日。说到抗日,有人会说宫前这老山窝日本鬼子很少,你抗什么呀?抗日工作是多种多样的,拿枪上前线是抗日,在后方搞生产也同样是抗日。我们知道在战场上和日本人拼命的战士,要吃饭,要穿衣,要弹药,要兵员,这些都是靠后方支援的。如果没有后方,前方是不能打仗的。我们八路军百万将士在前方流血拼杀,急需后方的支援。抗日人人有份,有钱出钱没钱出力,搞好生产多打粮食也是抗日。抗日区政府是保护人民利益的,只要是抗日的,不管军民等都将受到保护。在这里我还要告诉那些心怀恶意的人,抗日区政府是扎定了,日寇不投降,我们就永远扎下去。”
张区长的话已经说完,可大家似乎还没有听够,硬硬地愣住了。短暂的一静,又好像明白了什么,于是一阵急风暴雨般的掌声热烈地响了起来……
一连几天,张区长和乡亲们一样,在山坡上的田地里扑打蝗虫。天刚麻麻亮他就起来上山,中午也不休息,饥了啃口自带的干粮,渴了喝口泉水,傍晚天已黑净了,他才拖着疲惫的身子走下山来。
辛苦点倒没啥,奇怪的是蝗虫好像越打越多。
这两天他一直在想这个问题,也曾到地里去查看。怪呀,昨天落地一层的蝗虫,今天却寥寥无几。这东西真能死而复生吗?他抓起一把细细验看,发现凡死了的都是开膛破肚,或肚皮冒水的。肚皮没伤没冒水呢?他弄不清。于是他又跑到一块刚扑打过的地里,抓起一把,呀,这里边有一多半的身上没有伤痕,只是被柳条抽昏而落地的。他又抓住一只飞来的蝗虫,无意间触摸到了它的头部和翅膀,他感到有一层硬硬的东西,这是一层甲呀,这……啊,他的心一下子亮了。
这时,他感到快活极了,几乎想奔上山头呼喊几声。但他没有。冷静下来的时候,他在心里说,看来单单把蝗虫扑打下去是远远不够的,还必须把它治得反不过气来。至于如何把这些遭害人的东西真正弄死,他一时还拿不出好的主意。
想到这儿,他抬头朝四处张望,却见近处块地里围着一群人。他迈步往那地里走去,透过稀疏的人群,见郝三娃扎跪在地,面对着一炷香,口中念念有词,像在祈祷着什么,“郝三娃,你又在弄什么鬼?”
“我在替乡人赎罪。”郝三娃瞧了张区长一眼,慢慢站起身,恭恭敬敬作了一个揖后,才弯下身子拍了拍膝盖上的土。
“乡亲们有什么罪?”
“初时,我说蝗虫不能打,张区长率众闯入我家逼着我说蝗虫该打。这不,打了几天了,你打的蝗虫在哪儿?非但没有扑灭,反而使蝗虫越来越多。这分明是老天爷在惩罚我们,乡亲们,天命不可违呀!”
“我们共产党、八路军以人民利益为重,从来就不相信什么‘天命’,对危害人民的事,我们就要犯上作乱,包括玉皇大帝,也包括你郝三娃。前段我们对你宽大为怀,并不是软弱可欺,你不改恶从善,反而继续为孽。我告诉你,如果你不思悔改,我一定要发动群众清算你。”
郝三娃冷笑了一声:“请问张区长,你清算我什么?”区长上前一步,指着郝三娃说:“清算你剥削穷人的剥削账,清算你压迫穷人的压迫账,清算你与区政府作对的捣乱账。”
郝三娃听后,头摇得像个拨浪鼓,连声说:“没听说过,没听说过。”
“没听说过今日就算给你捎个信儿,账嘛改日再算。”说到这儿,张区长抬起头对着大伙儿说道:“几天来,乡亲们扑打蝗虫很是辛苦,可是蝗虫不但没有扑打下去,反而越打越多,这件事是奇怪的,但这并不是什么老天爷在惩罚我们,而是我们消灭蝗虫不彻底所造成的。蝗虫有一个硬甲保护自己,当我们用柳条或别的什么东西击打时,它的心脏及要害部位并没受到损伤,虽然落到地下,却没有真死,等一段时间缓过气儿,就活过来了。这就给我们造成一种错觉,好像蝗虫是永远打不完的。”
这时,一个战士跑过来说:“张区长,尤二在田里点火。”点火?一股抑制不住的喜悦在张区长的心头轻轻触动了一下,他稍一镇静,说:“走,咱们去看看。”
这是一块宽大的麦田,绿油油的麦苗已经饱肚了,但是可恶的蝗虫却将麦叶麦杆啃得残缺不全。在碧绿的麦田里,尤二脱去棉袄,只穿一件白布褂,高挽着的双臂撑着一面宽大的簸箕。他弯腰骑着一垄麦往前疾走,两手不停地抖着,那蝗虫很自然地落入簸箕,只要落进去,就是能飞能蹦也休想逃脱。当他从那头走到这头,簸箕里已有许多蝗虫。地头空地上有一堆大火,他将簸箕一伸,蝗虫就落人火里。
地那头也有一堆大火,尤二抖着簸箕往那头走去。地头埝边站了许多人,他们兴奋地看着,笑着,议论着。
“尤二这个办法好呀!”张区长步入麦田,尤二看见了,忙将簸箕往别人手里一塞,迎了上去。在麦地当中,两个身影紧紧地拥抱在一起。
这天下午,各沟小岔都燃起了熊熊大火,三五天后,宫前、雁翎关一带蝗虫基本消灭。
就在那天夜晚,郝三娃骑着一头毛驴偷偷地逃进了县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