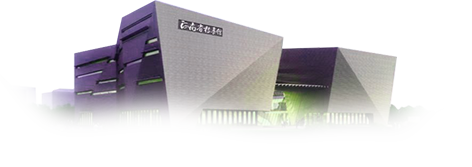红色记忆之寻找三门峡最早的党支部
时过多年,今年90岁的刘全生仍然能清楚回忆起,1984年前,豫西地区(现在的三门峡地区)的党史一直以抗日战争时期为起点进行记载,豫西地区的“红色渊源”在学术界也一直存在争议。为寻找到豫西地区当年第一粒红色火种,1984年和1985年,在陕县党史办工作的他,跑遍了豫西山区的沟沟坎坎,费尽周折,内查外调,终于使这个问题有了答案。
在豫西党史研究上有个关键性的人物,他就是在建党初期曾在豫西指导过工作、后来调到北京的革命元老罗章龙。当刘全生在北京见到这位至关重要的人物时,罗章龙同志由于年迈,对半个多世纪前豫西地区革命风云的变幻只留下了模糊的记忆。在北京罗章龙的寓所里,刘全生根据自己调查了解到的历史背景,与罗章龙一起重温了那段往事。罗老的思绪渐渐又回到了在豫西战斗的那些日子……当他明白了刘全生的用意后,很郑重地向刘全生推荐了自己当年亲手编著的两本珍贵的图书:《椿园泽记》和《中国北方工人运动资料选编》。在这两本当年并不引人注目的书里,刘全生终于找到了三门峡历史上红色火种的起源。
1921年7月,中国共产党诞生。新生的中国共产党积极领导工人运动,掀起了中国民主革命的高潮。当时的陇海铁路由法国和比利时控制,外国总管不断苛扣和降低工人工资,虐待工人,激起了沿线工人的极大愤怒。1921年11月,陇海铁路工人爆发了全线大罢工。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对陇海铁路工人大罢工很重视,他立即派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部主任罗章龙前来指导罢工。罗章龙秘密从北京到郑州转洛阳,由洛阳铁路工会负责人游天洋(罢工领导人,中共党员)、白眉珊(中共党员,时任陇海铁路常委兼秘书长)等陪同,乘坐一节由陇海铁路工会指派的火车头亲临陕县观音堂指导工作。当时,陇海铁路仍在修建中,东边到江苏徐州,西边终点站就在河南省陕县观音堂。当时,从观音堂往西至老陕州城的铁路仍在紧张施工中,铁路路基两旁搭满了工人休息的道棚。正在筑路的工人(当时称道棚工人)纷纷响应罢工号召,但由于没有先进分子组织,罢工活动进行得非常松散。另外,还有许多工人对罢工信心不足,一直 担心罢工后挣不到钱。罗章龙坐着工地上的压道车,沿铁路路基调查,直至会兴镇(现湖滨区会兴镇)。在一部分先进分子的协助下,罗章龙把道棚工人编成小组,并分组对他们进行培训学习,从而提高他们对坚持罢工的认识。最后,陇海铁路全线罢工坚持了7天,取得了决定性胜利。
罢工结束后,罗章龙回到北京,向党组织汇报了罢工工作,讨论了在河南创建党支部的问题。最后北方区委认为在河南建立党支部非常必要。于是,正式在郑州、洛阳、开封以及陕县观音堂几个重要的火车站创建了河南最早的党支部,每个支部2至3个人。当时在观音堂当搬运工的符敬宗、水湛寅在罢工过程中表现得非常积极,被组织正式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,并成立了观音堂车站党支部。作为县级地方党支部,观音堂车站党支部与郑州车站党支部、开封车站党支部、洛阳车站党支部一起直属中共北方区委。
根据罗章龙提供的线索,刘全生开始对符敬宗和水湛寅的情况进行调查了解。为查清符敬宗和水湛寅的身份,20世纪80年代中期,刘全生开始在观音堂附近打听,寻找一些上了年纪的老工人,请他们来追述那遥远的历史。老人们总能依稀记起当年亲切的“水哥”。在观音堂,刘全生找到当年在火车站做炊事员的高金殿老人,在刘全生的启发下,高金殿恍然大悟般想起以前的事情,说当年罢工召集工人开会时有两个人特别积极,并不知道他们叫什么,大伙喊其中一人为“水哥”。这两个人在工人中有相当高的威信。罢工时,他们召集大家到车站附近的骆驼房开会,对大家说,没有工会的号令,决不复工。听说符敬宗是洛阳的,刘全生又亲自到洛阳的符家屯,在符家的家谱中查到了符敬宗,符家的老人也有人记起,符敬宗以前确实在陕县观音堂赶马车送过货物。
刘全生说,随着陇海铁路向西延伸,红色火种也逐渐向西蔓延。1924年,陇海铁路修到了陕州城,符敬宗、水湛寅也到了陕州城。1927年“四·一二”反革命政变后,按组织要求,符敬宗和水湛寅分别进行了分散隐蔽,但革命的火种从此留在了豫西。民主革命时期,豫西一带的革命组织多次遭受白色恐怖势力的摧残,多次濒临危境,但“星星之火,可以燎原”,豫西地区的革命浪潮一浪接着一浪,永不停息,直至迎来新中国的成立。(聂建英)